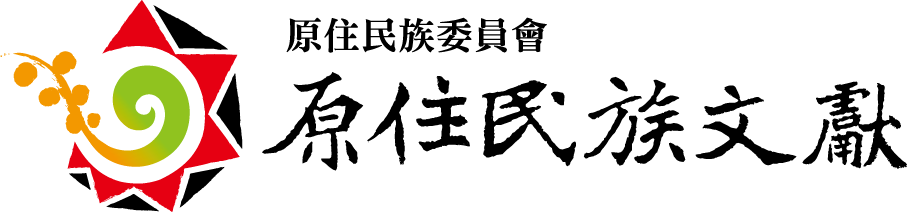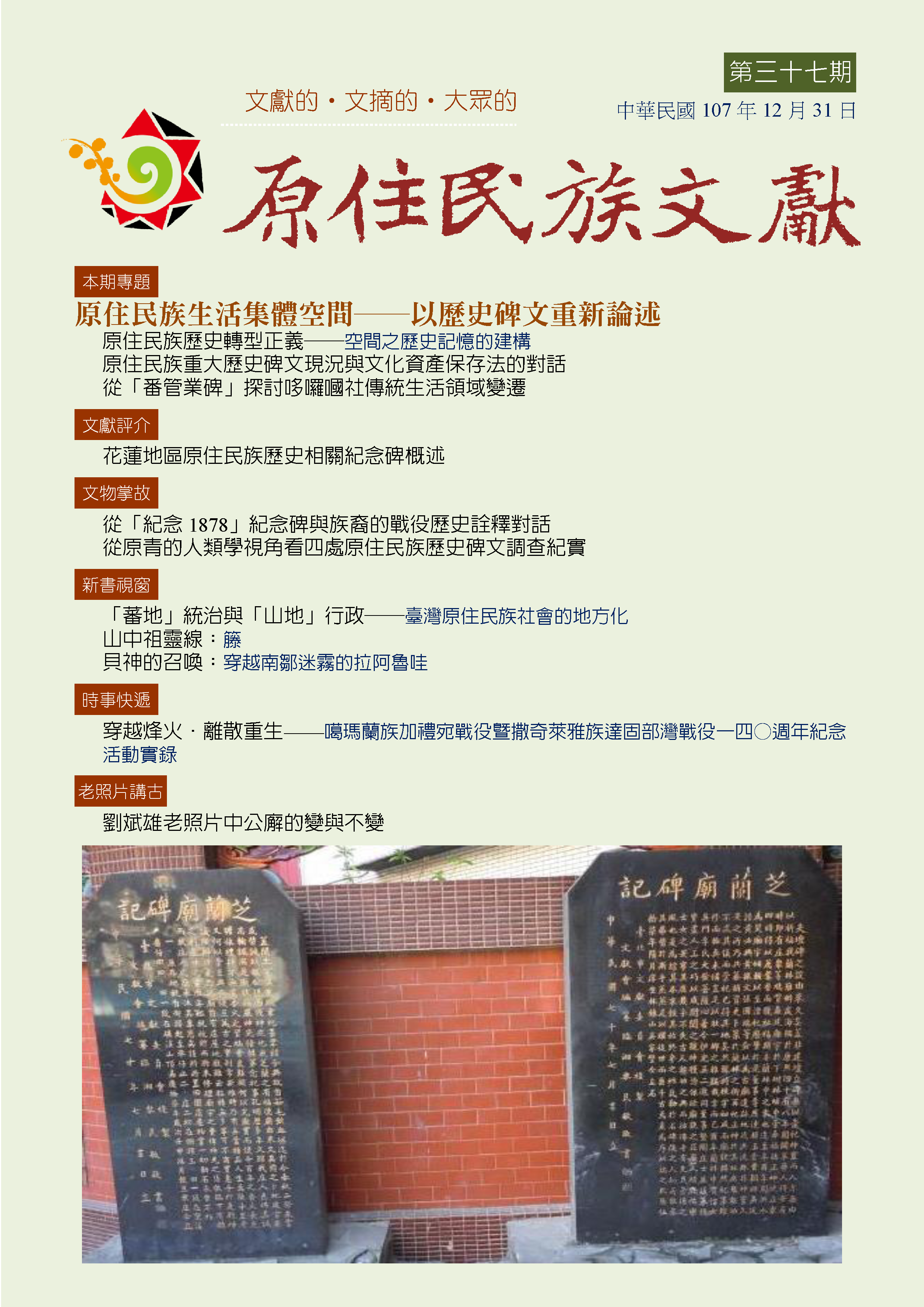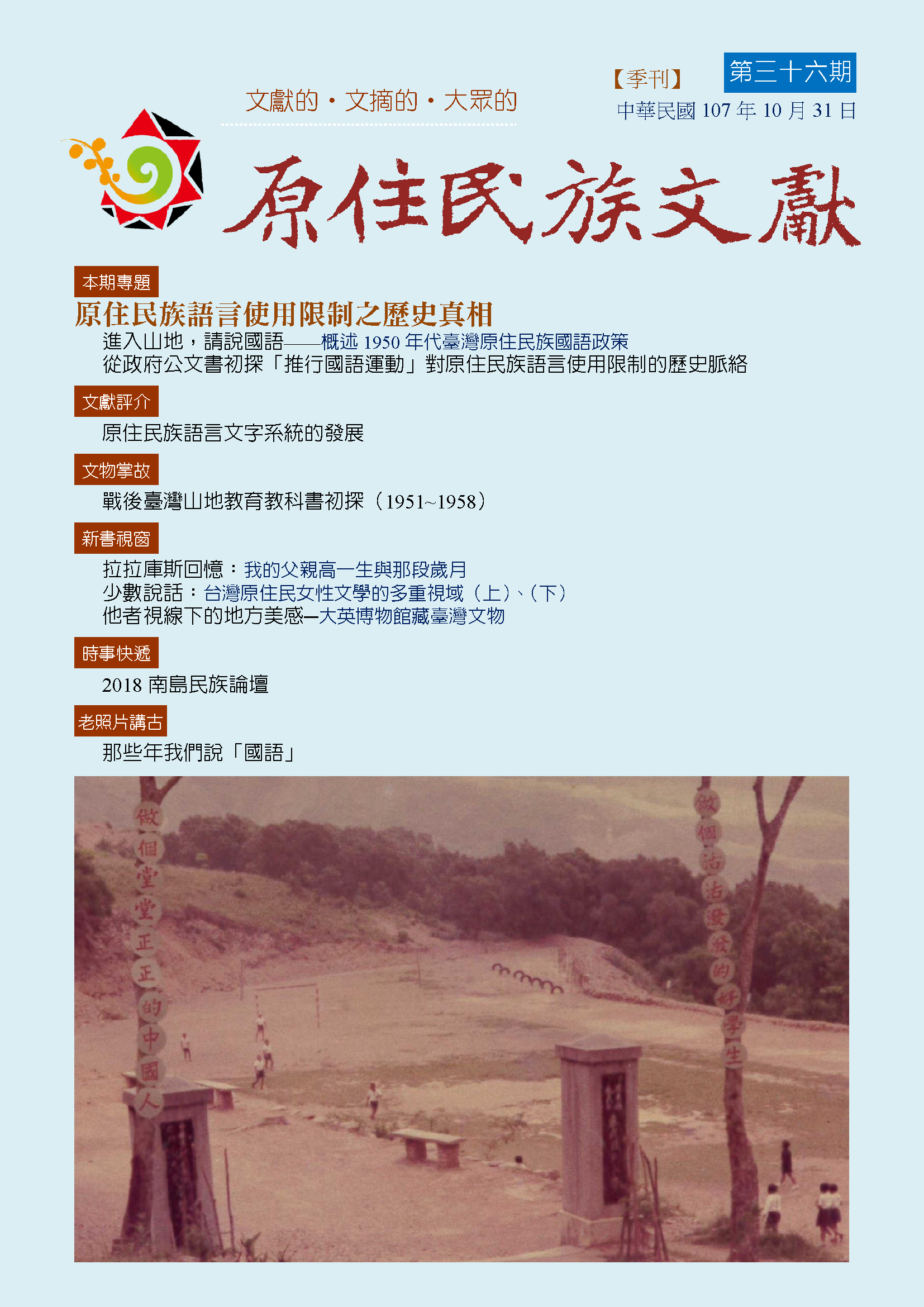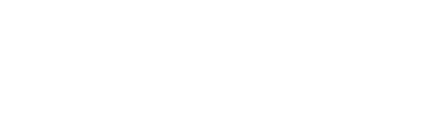歷史期刊
原住民族生活集體空間─以歷史碑文重新論述(2018/12 第37期)
本期專題從歷史碑文的角度來重新論述原住民族生活集體空間,先對如何透過碑文建構有原住民族歷史記憶的空間與族群認同,達到建立轉型正義中的多元史觀進行概述;再透過目前調查中的歷史碑文現況,以現有文獻的記錄與分析,試圖與《文化資產保存法》規範來討論碑文的設立脈絡;亦從「番管業碑」來探討平埔族群哆囉嘓社傳統生活領域變遷。同時,介紹花蓮地區日治至戰後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紀念碑類型,以及2000年之後所設立的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此外,從設立於花蓮市國福里的「紀念1878」紀念碑,展開與族裔的戰役歷史詮釋對話,並以原青的人類學視角,來看四處原住民族歷史碑文調查紀實。最後,藉由劉斌雄教授拍攝的平埔族群公廨老照片,在新、舊公廨對照下,分析變與不變的所在,並對這批珍貴影像文獻的運用提出在地觀點建議。
原住民族語言使用限制之歷史真相(2018/10 第36期)
本期專題著眼於臺灣戰後時期「推行國語運動」政策對原住民族語言使用限制的影響,透過自195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國語政策的概述,以及政府公文書的爬梳,勾勒整體政策執行脈絡,以理解原住民族語言流失的原因。此外,也介紹原住民族語言文字系統的發展演變,與探究1951年至1958年山地教育教科書的編輯理念及態度,更藉由老照片講古,述說當時在國語和族語間不斷轉換而後回歸族語文化復育的時代樣貌。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他者與自我(2017/12 第35期)
在第一個統治政權到來台灣之時,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處於強調聲韻運作、而非文字的時期,因而並未發展出表音或表意的文字系統。隨著歷代政權的語言政策介入,留下了原住民族語言各個時期的樣貌、也進而影響原住民族語言的發展。
本期專題關照的是:一、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他者」如何作用:荷蘭人統治之下發展的臺灣教會語言如何推展?日本時代理蕃警察所接受的原住民語言訓練如何進行?以及,二、原住民族主體「自我」的應對和回應: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及語言活力如何展現?以宜蘭泰雅族的克里奧爾語為例,原住民族如何在社會文化鉅變的背景下,依舊保留其語言的韌性和彈性?
本期專題關照的是:一、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他者」如何作用:荷蘭人統治之下發展的臺灣教會語言如何推展?日本時代理蕃警察所接受的原住民語言訓練如何進行?以及,二、原住民族主體「自我」的應對和回應: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及語言活力如何展現?以宜蘭泰雅族的克里奧爾語為例,原住民族如何在社會文化鉅變的背景下,依舊保留其語言的韌性和彈性?
族群邊界的互動、變遷與重構(2017/10 第34期)
20世紀以來,透過學術調查的分類、政府的民族識別工作、以及族人自我的認同歷程反覆形塑,台灣原住民族成為現今被認定的16個族群。本期欲呈現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跨族群的文化互動、生計樣態和變遷、族群身份的形成和構建。
本期專題透過鄒族的赤崁經驗,述及鄒族遷徙路徑與途中族群的關係;以及噶瑪蘭、撒奇萊雅、阿美族族在歷史上交纏的對峙與共生;更有噶哈巫族族與賽德克族間頻繁的交易、馘首;甚而,南投布農族傳說綠豆的種子與名稱來自於西拉雅族、目前還成為一家姓氏;最後以「誰是斯卡羅?」的提問,重新審視恆春半島複雜多樣的族群關係和身份實踐。
本期專題透過鄒族的赤崁經驗,述及鄒族遷徙路徑與途中族群的關係;以及噶瑪蘭、撒奇萊雅、阿美族族在歷史上交纏的對峙與共生;更有噶哈巫族族與賽德克族間頻繁的交易、馘首;甚而,南投布農族傳說綠豆的種子與名稱來自於西拉雅族、目前還成為一家姓氏;最後以「誰是斯卡羅?」的提問,重新審視恆春半島複雜多樣的族群關係和身份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