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的歷史書寫與「史觀」
本期專題
第24期
2015/12
文/詹素娟
自從「歷史課綱微調事件」造成社會爭議後,歷史用語與歷史事實、詮釋觀點的複雜關係,歷史教育與政治現實、國族意識的糾葛,就受到各界注目與激昂熱烈的討論。歷史教科書中關於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內容的偏頗、欠缺與不足,以及原住民歷史的主體問題等,也在原民團體發聲後,引發各種迴響與論辯。在這段期間的眾多論述中,頻繁出現「史觀」二字,甚至將史觀簡化為政治傾向,藉以強調不同意識型態的對決──如「臺獨史觀」vs「中華民國史觀」或「皇民史觀」vs「國族史觀」等。原民朋友則拋出「原住民族史觀如何可能?」或「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臺灣史如何可能?」等議題,使「史觀」的口角爭鋒更具多樣性。然而,「史觀」究竟何指,若不能多加思考或試圖釐清,免不了各說各話,只能產生更多的紛爭,本文即受命要來談談這個複雜的課題。
簡要來說,所謂「史觀」,既可視為對「歷史」的觀點,也指涉時間觀、對「歷史」的概念或發展的邏輯,而兩者都可以問:「誰的歷史?」。就前者而言,這個觀點的主體是「誰」、指稱的「人群範疇」為何,必須有所界定,如作為集稱的原住民族或個別單一的民族;而此一「人群範疇」既是自我的界定,更不免是國家建構、殖民統治外塑的結果。由於主體不同,看到的歷史也不會一樣,以致於同處一個社會,卻有多種歷史觀點的記憶並存,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對立、爭奪與壓制,也可以是相互尊重與理解。再者,一旦強調主體,必然有族群身分的問題,所謂「我族寫我史」,似乎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但「非我族類」是否就產生不了具有主體性的「史觀」?恐怕是一個更艱澀的疑問。以後者來說,除了主流人群常提起的進步史觀、循環史觀、開發史觀、華夏文明史觀外,原住民各族也自有一套來自文化深處的時間觀與相應詞彙、理解歷史的方式、傳遞歷史的媒介;如布農族以palihabasan(述說過去)、linahaiban(以前走過的路)等關鍵詞對歷史的分期(註1),就不同於阿美族年齡組織命名背景所反映的歷史記憶(註2),而馬淵東一在將原住民社會地理知識類型化為「生活圈」、「見聞圈」、「傳說圈」時,則強調「這種地理知識已經屬於歷史知識的範疇」了(註3)。由此,作為歷史概念的「史觀」,因與歷史文化的深切勾連,則歷史主體究竟是「誰」也脫離不了干係。綜合前述,若仍以布農族為例,既可以原住民族此一經由原運取得、納入憲法之集體身分,亦可以跨部族形成的布農族裔,甚至以特定部族如Isbukun等,作為突顯史觀的主體;同時,因為族屬身分、族語熟諳與文化體會,遂能理解、傳達布農族的時間觀、歷史觀,書寫「我族」的歷史。換句話說,所謂「史觀」的兩種面向,其實關係交織、互為因果,難以分離。
釐清「史觀」的內涵,目的不僅在用於「主體」的宣稱,更重要是如何應用在歷史書寫上,娓娓道出一個屬於原住民的故事。然而,歷史書寫是極複雜的作業,必須大量收集資料、審慎考訂文獻,反覆閱讀,在字裡行間抽絲剝繭,交叉排比,始得以建立基本的歷史過程與相關細節,作為進一步書寫之用。但對傳統係屬無字文化的原住民族來說,文字史料往往是他者的記錄或國家治理、征伐的文書檔案,其記載的時間、地點、數據、法令、制度、人名等可能具體客觀,但觀點、用語卻大多充滿偏見、誤解、猜測與扭曲,或基於國家利益、國防安全、政令宣導等前提,貶抑受治者的智慧,強調治理的功能,忽略少數人群的文化特性、在地立場與心理動機。因此,若要從事具有原住民史觀的歷史書寫,如何在主體缺席的文獻中萃取出原住民思惟與立場的素材是首要之務,而最有力的解決之道當然是由原住民自己來書寫。然而,書寫者的族裔身分是否就能克服缺乏原住民「史觀」的難題?或只要譴責國家或殖民者,或強調原住民行動者的動機或心態即可達到?
在此應該舉一個例子,日治末期,針對日人徵調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戰場的事例,有謂日人在霧社事件後改弦易轍、視「蕃」如子的治理方式,使原住民首次意識、認同到國家的存在,而志願爭戰、效忠國家;也有人認為此係日本警察強制動員,迫使族人從軍的結果。前者顯然是殖民者立場的解釋,後者則乍看似有原民主體於其中;但就包含許多細節、各種力量相互拉鋸的歷史事實而言,真的可以如此簡化嗎?只要妖魔化日人統治、就能找到原民位置,這與昔日妖魔化原住民文化習性、以突顯外來人群「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合情合理,其實是類似的邏輯。而暫不論歷史情境當下的「真相」如何,試問:即使因日人統治、意識到國家存在而改變了世界觀,這樣的「事實」是否就欠缺族人的主體性?歷史書寫者若因殖民情境而窄化、政治道德化被統治者的轉化或選擇,不也是一種歷史解釋的暴力?我們不應忘記2006年2月24日臺北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遭當時臺北縣政府強制拆除事件,即是一個關於「如何記憶過去」、挑戰「記憶的自由」作為族群不可侵犯權利的案例(註4)。當烏來的泰雅族人基於歷史經驗與自主意願,建碑紀念屬於自己、跨越時代的歷史記憶時,是一種「史觀」的展現,誰也不能曰其不宜。再以1960年出版的《山地社會》一書為例(註5),由該書內容的敘事觀點、資料使用與政策建議來看,若非作者許秀明在序中自稱「筆者是一個山胞青年」,讀者實不太能區別其與張松的《臺灣山地行政要論》(註6)或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出版的《進步中的臺灣山地》(註7)等文獻有何差異。因此,書寫者固然擁有追求主體的身分條件,但在民國四十年代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又怎能要求作者的書寫符合21世紀臺灣社會氛圍對「史觀」的期許與要求呢?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出版的《進步中的臺灣山地》。(圖片提供/詹素娟)
準此,「史觀」豈有標準答案,亦不應以他者、政治道德或殖民嫌惡而強求於記憶相異的不同人群。換句話說,身分與認同、記憶與文獻、史觀與真相、書寫與詮釋,幾者之間錯綜複雜,其背後更有時間軸帶動的價值變遷,不宜以政治道德、價值判斷輕易綁架;而多重史觀若能並存,即使價值反轉,也應包容納入,才是歷史理解的真正解放。
再者,具有原住民身分的歷史書寫者,除非以族語拼寫,都有使用外來者文字工具的問題。惟語文的學習與應用並非純粹的技能,而是教育文化接觸濡染的結果;以日治時代警察刊物《理蕃之友》為例,該刊有若干作者實為本地原住民,但姓氏已改,其投書、短文、札記都以日文書寫,且大多呈現編者所欲展示的統治成效與受治者的感恩。戰後雖改換為漢語中文,但語言所承載的政治壓制、文化霸權,卻還是一貫的,如前所述許秀明的《山地社會》。此因書寫者的主體與書寫語文的客體之間,糾纏著殖民與被殖民的複雜關係;而「非我族語」的使用,讓「史觀」的追求有更多需要克服的困難。


日治時代警察刊物《理蕃之友》。(圖片提供/詹素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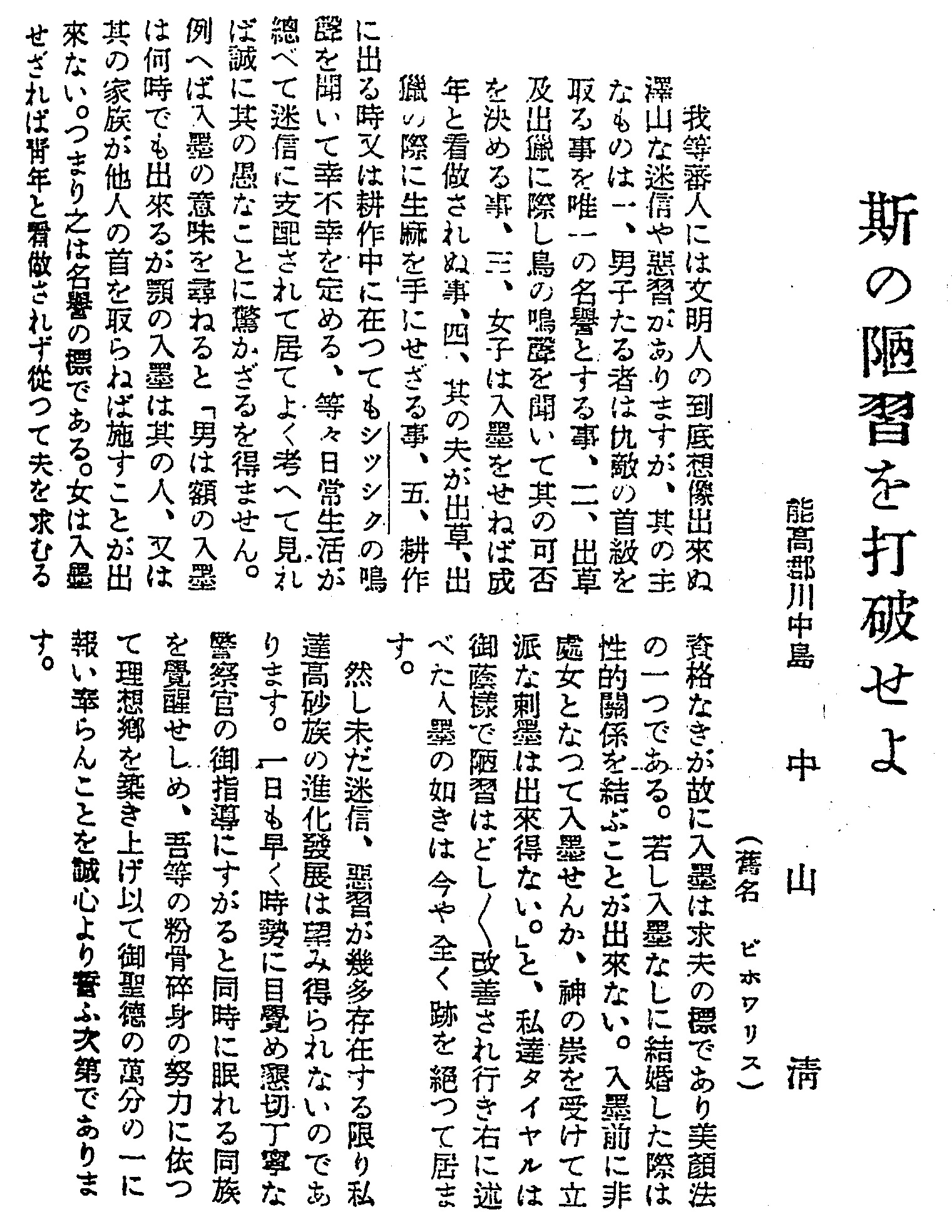
《理蕃之友》第三年六月號片段。(圖片提供/詹素娟)
人類學者王梅霞在泰雅族苗栗麻必浩部落關於高砂義勇隊參戰歷史的訪問中發現,族人在不得已被徵調前往戰地時,部落會以豬鼻為祭品,對lyutux說:「這戰爭是日本人和美國人之間的事,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所以和我們無關,我們帶著gaga去從軍,請你保佑部落的人平安歸來。」族人以傳統文化價值理解世界的變動、國家的角色,並藉由儀式表達謹慎的反抗(註8)。這樣的描述,比無限上綱的「史觀」宣稱,更讓我們看到不同於狹隘設限史觀的原住民歷史細節與文化彈性。人數偏少的非主流族群,可千萬不能小覷「弱者的武器(註9)」啊!
(註2) 黃宣衛(2005)〈宜灣阿美族的時間、歷史與記憶:以男子年齡組織與異族觀為中心的探討〉,
(註3) 馬淵東一(1988[1941])〈山地高砂族?地理的知識?社會•政治組織〉,《馬淵東一著作集》,
【作者介紹】

詹素娟
土生土長的臺北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長期從事臺灣原住民史、區域史與歷史教育研究,希望能透過「歷史」,探索各種時空脈絡下,不同人群與臺灣土地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學徒的熱情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