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雅族有自己的文字嗎?──一名西方傳教士的「文明原住民族」打造之旅
本期專題
第42期
2020/09
文/李慧慧
李慧慧
桃園市原住民族行政局原民福利科科長
I.前言
臺灣原住民族一向被認為是以口傳方式溝通交流、傳承知識,是無文字傳統的族群。然而,孫大川指出早期臺灣原住民並沒有文字,部落傳播主要以「口傳」形式進行,透過聲音語言傳遞訊息與表達情感。除口傳以外,無聲的編織、服飾、紋身、石板屋等藝術表現,亦承擔著原住民傳統社會的傳播責任,生動的「書寫」了早期原住民的主體世界(孫大川 2000:158)。也就是原住民傳統物質文化與藝術的表現,亦是一種書寫傳播的方式。
17世紀,荷蘭、西班牙佔領臺灣,西方傳教士因傳教需要,以「羅馬拼音」翻譯聖經、聖詩及製作語言教材,以利正音文字推展語言,類此「教會版」書寫,賀安娟稱此為「教會語言學」(賀安娟 1998:81-120;Sing ‘Olam 2013: 18-19),使臺灣原住民語言出現了「文字化」,在新港社以西拉雅語文呈現被發掘的「新港文書」是目前學術界定論為最早文字化的文書,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與貢獻(巴瑞齡 2009:47;李壬癸 2002:1-68;黃秀仍 2005:51)。
從臺灣原住民族語發展歷程來看,1987年解嚴之後,原住民族語言保存才開始受到政府重視。1解嚴前,政府採行同化政策致語言快速流失之際,幸有外來傳教士與在地文化逢遇,基於傳教需要以羅馬拼音記錄與保存族語,一來使得原本無文字傳統的族群,透過局外人的創意,讓文化得以保存與傳承,二來宗教的權威在習得在地語言與文化,使得原來的局外人轉換成為局內人。傳教士為了達成宣教目的,以羅馬拼音翻譯聖經、編印族語教材,創製了族語「文字化」的拼音系統。
文字讓人迷惑。有些人認為,文字標幟著文明,沒有文字顯得落後。然而,文明與文字並不一定畫上等號,但幻想有文字可以讓族群比較文明與進步,不是只有原住民,西方傳教士也是。桃園市唯一且偏遠的山地行政區復興區就有一位巴義慈神父(Fr. Alberto Papa O.F.M.)站出來告訴泰雅族人:「你們是有文字的,就在織布當中」,這樣的發現,族人聽了如何反應?一般人怎麼想?
首先,一定會好奇為什麼是外來的神父發現文字?而不是泰雅族人自己出來指證?外人竟比族人更了解泰雅族?這有幾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神父對古文明文字向有研究,知道的比泰雅族人多,因而沉埋多年,連族人長輩都不知的文字,被他獨特地發現了。但,此前提是泰雅族真的有自己的文字。第二個可能是神父為了宗教上的信仰與動機,相信泰雅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文字,因為從其他古文明來看,不少族群有自己的文字,泰雅族也一定有,只是失傳了,所以編織這個發現。當神父從織布中解密,說出泰雅族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成為部落文化核心的重要人物,使他熱心傳播的宗教更具說服力,更能取得泰雅族人的尊崇與信賴。這兩種都是可能的動因。當然,也有第三種可能,就是神父對編織圖案特別有興趣,偶然間意外發現這些就是文字,無心插柳,也無宗教動機,且非因有深厚的古文字研究。第一和第三種可能,都是本來就有文字,後經神父發現,而第二種可能,則是無中生有,前者是發現,後者是發明。
然而,不論是發現還是發明,這中間可能都有一種潛存的意識,即是認為有文字的族群是文明的,是進步的象徵。不過,這種想望是不是一種迷思?有文字就比較文明,沒有就比較落後?但不論有或沒有,本文想探討的是,當原來無文字傳統的族群被指出有文字,現實生活會出現什麼變化?後續產生什麼效應?本文聚焦於探討來自義大利的天主教神父─巴義慈,從泰雅族的傳統織布中發現文字,以及2013年自行以英文出版的Picture Writings on Atayal Tattooed Women’s Clothes in Taiwan一書之內容(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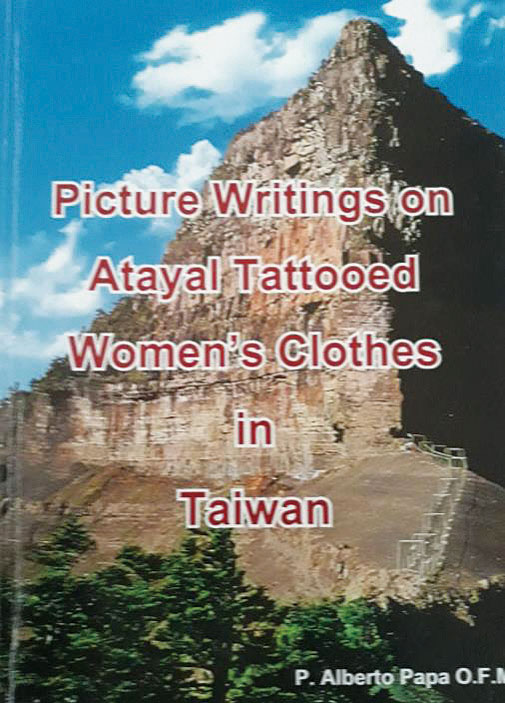
圖1 2013年巴神父以英文自行出版新書封面。
II.織品中的文/數字
巴神父生於1935年,在1963年時,隨著天主教梵諦岡教廷總主教,自義大利到臺灣山區原住民部落傳教。多年來一直待在桃園市的偏遠山區―復興區2泰雅族部落宣教,落腳三民天主教堂,前後逾半世紀。他初抵臺灣時,曾短暫到新竹學習國語,但感到國語無法順利在部落傳福音,且深切了解部落語言承載文化精髓,必須學習泰雅族語,方能拉近與部落族人的距離,不致隔隔不入或讓人高不可攀,惟有深入理解並參與當地泰雅族人的生活,如泰雅族日常殺豬祭祀、婚喪喜事等,受邀者才被視為是部落自己人。
巴神父足跡踏遍復興山區的角落,努力學習當地語言,說了一口流利泰雅族語,並從語言習得並傳承泰雅族文化。以羅馬拼音將聖經翻譯為泰雅語,也編纂《泰雅爾語文法》(1986)、《認識泰雅爾母語》(1993)、《泰雅爾語研習初級本教材(第1冊)》(1995)、《泰雅族母語初級讀本-泰雅爾字母輔助教材》(1999a)、《泰雅族母語初級讀本》(1999b)、《泰雅爾語研習初級基本教材第二冊》(2000a),《泰雅爾語字母輔助教材簡介手冊》(2000b)等,這些泰雅族語教材不僅廣泛運用於教會,也做為國中、國小學習族語的教材。傳教士在傳遞外來文化時,也保存了部落文化。
巴神父努力將泰雅族語用羅馬拼音方式讓它文字化,使用西方書寫系統翻譯經文,最初動機的確與傳教有關。神父族語文字化的努力,對於本身沒有文字的臺灣原住民族而言,不但帶來了羅馬拼音字母,還幫原住民拼寫了原本沒有文字的語言,不僅翻譯聖經,並編製族語字典,還將泰雅族人奉為族群文化核心的道德規範(gaga)與聖經義理相連結,種種作為受到當地族人的肯定及讚譽。他從局外人狀態,經由努力學習在地文化,成功地進入內部核心,並再跨進一步,超越在地人,用新的形式傳達在地人的文化,創造了局外人融入並改寫在地文化的成就。由於對泰雅族文化薪傳的貢獻,受族人敬重,獲地方政府頒贈「復興鄉榮譽鄉民」及「桃園縣第一屆桃園奉獻獎」的殊榮。
在族語傳承上有貢獻的西方傳教士為數不少,但巴神父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是,他有另一個重要的發現,即是從婦女的織布中,發現了泰雅族有文字。泰雅族的織布彷如印刷機一般,織布中的整幅圖案成了有意義的語言文字,巴神父將這些圖案拆解出基本單元或符號元素,進而對這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加以詮釋。巴神父自有一套獨門的邏輯與合理的解釋,例如,他說的織布中的1(qutux)與2(sazing)數字,1是「∕」一個向上的符號,2是「∖」一個下降的符號,所以3(cyugal)就是1與2的結合「〈」或「〉」這樣的圖案,其它數字依此類推,並說「/」有進一步的意思,代表男性,因1的發音有無限存在的意思;「﹨」這個下降符號代表女性,發音蘊含有這裡是生命富饒之地,男與女的指涉,是根據1與2的泰雅語發音而來,再推而延伸,1與2(男與女),象徵了泰雅族人的生命,當1與2結合,而成「〈」這個形狀時,雖然形成3,但這個3的發音分別有「生命的直立存在狀態」以及「一種開放的真實動作」,若是結合成這樣的3「〉」,這個發音又有指涉「一個結合的關係」。因此,再深入地看,「〈」這符號代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結合為一,特別是指心靈與思想的狀態;而這個符號的3「〉」,也代表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合一,但偏重在指身體的結合,一個指心、一個指身,當這兩個3再結合成為一個菱形時,也就是6(mtzyu'),它的發音表示是「泰雅族人的家庭結構」,也就是指「家」。菱形6,還可指涉一塊泰雅布料,用來遮掩身體私密部位的布。
上述1、2、3圖案只是簡單一例,巴神父所說的泰雅族文字還有比幾何圖形的數字更複雜的圖形組合,筆者不多引述。他獨特的理解織布符號所具特殊意義,將這些符號組織成一套有意義的說法,並結合泰雅語的發音,把泰雅族文化與生活融入到這套文字系統的「說文解字」之中,成為一組有意義的文字系統。巴神父理解圖案文字的邏輯,也與他的宗教信仰有關,例如在桃園市復興區的幾座天主教堂牆上,貼有一些幾何符號,這些符號對於族人教友來說顯得陌生,也不知是什麼意思,但教堂的管理者表示,巴神父認為泰雅族的數字與天主教的符號相似,甚至有相同的意義(李懿宸 2010:221)。(圖2)

圖2 桃園市復興區三民天主堂內以巴神父自織布中幾何圖形發現泰雅族的數字佈置。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19/5/5)
III.前夢中夢到後夢
巴神父發現了連泰雅族都不知道的文字密碼,有點像考古學家突然發現了深埋地底的千年古物,有著興奮的成就感。泰雅族有沒有文字?語言學者可能更關心這個的答案。但筆者留意的,不是文字本身到底是真是假,反而是文字之外衍伸、開展的現象。
在他書中說明所發現的文字系統時,經常嘗試連結閃語族語言以及基督宗教上的相對應事物,這麼做是暗示泰雅族與這兩個系統(古文明與宗教)之間的關係,顯示泰雅族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如他在解說泰雅族圖象文字時,多次指涉這個圖案在西奈時期或埃及文字、希伯來文字、希臘文字都有相似的符號與意涵。巴神父將所知道的上古史、文字學、宗教史等納入對泰雅族文字的合理化之中,說明其根據與來源,也企圖藉外來權威樹立巴式說文解字的正當性,重新賦予泰雅族文化不一樣的起源論,是一套與世界接軌,與全球文明發展網絡相連的概念。
「世界框架」下的架構,筆者稱其為「前夢」的設定,藉此建造族群自我認知,這是局外人帶進的一套信仰系統。泰雅族在其中感受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與歸屬感,以及嶄新的自我定位。這一套設定之所以可能,即是因為有了「文字」,以及因文字而與其它文明產生連結所奠下的基礎。
另外,還有「中夢」的發想與「後夢」的實踐,三者共同連結了夢境。所謂中夢發想,意指在巴神父書中提到這一套文字解說是他多年跟泰雅族長者學習語言過程中,逐漸了解發音與字義的關連性,即是從語音的組合、結構中獲取它的意義,如字首發音含有什麼意思,加上字尾發音的意義,共同組合成這個字的整體意義。有一天,他在思考某些字的音素連結所產生的意義時,剛好手上拿了一塊織布,織布上有「〈」這樣的符號,他試著解讀這個符號的意義,把這符號拆開成向上與向下兩單位,使他想起泰雅數字1與2的發音,發現不只形象上,這符號有著向上與向下的不同,同時在發音上,「t」這個子音在字詞中的位置,也顯示了有向上的意義。也就是說,語音結構跟文字意義有一定的邏輯關連。
他又注意到1與2兩個符號的結合,又形成了3「〈」,但為什麼?根據什麼原理形成?則未提及,或因受羅馬數字結構、其他古文字形成邏輯所啟發,讓他有了這樣的發現,並與泰雅語發音結構做連結。書上第69頁提到,他把這個發現與織布,拿去給一位泰雅族會編織的阿嬤(yaki)看,把他對織布圖案的發現與理解說給她聽,yaki聽完了之後說:「神父你解讀的很好,這是誰教你的?」神父笑說:「我是自己學習、觀察與領悟出的」。織布圖案會對應到一個泰雅族文字,以及對應到一個發音,這樣的文字發現,就這麼神來一筆地出現了。這就是夢中發想,既不是泰雅族長者告訴他的,也不是透過其它文物佐證建構起來。
神父自有一套邏輯理路,完成他對文字結構的論述,並非隨興亂湊而成。巴神父這段奇幻的文字旅程,筆者以「文字夢」來描述之,主要基於編織文字若不是真有,那整個故事極可能就只是巴神父個人的想像,或說是一場夢,以「夢」形容,不論真假,也都讓現實發生了變化。因此,這夢的形成與構築、落實,就有前夢、中夢與後夢的發展順序與過程。出了書就算後夢,讓文字夢得以實踐,而不是指更多的產出結果。也就是說,不是復興區泰雅族人全體接受,才叫做夢境成真。筆者認為巴神父所造的文字夢,是指在他可掌控的生命歷程中成就的夢想,並不因外在肯定與否,決定文字夢的成與敗。
巴神父的文字夢也曾經歷波折,送交中央研究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等申請出書未成,遂於2013年自行以英文出版了Picture Writings on Atayal Tattooed Women’s Clothes in Taiwan一書。巴神父的手稿能出版,有個偶然關鍵要因,是他因緣際會認識一位洪師父,其母是復興區的泰雅族,父親則是來自中國山東省,巴洪二位信奉的神祇雖不一樣,因均有宗教信仰,也都對古文字有看法與興趣,曾在角板山成立「古文字學舍」,定期相聚討論。二位相會共商,並非因彼此有深厚的古文字學基礎,也非因有地方耆老的大力支持。據洪師父說,只是因從各自的信仰觀點,認為許多事物都有共通之處,因而巴神父的發現,很快獲得了洪師父的共鳴,兩位都認同泰雅族是南島民族最古老的族群,也都認為織布裡的圖案就是泰雅族的文字。巴神父有了這位不同宗教朋友的支持,於是決定自行出版他的書,由洪師父幫他將手稿打字及電腦製版編輯,成書後,巴神父退休離開臺灣,因思念臺灣又回來,再次離臺前,於2013年赴法院公證,將這本書的著作權讓渡給洪師父。這本書的完成,也見證了不同宗教間的合作,以及保存古文字的努力。
巴神父的發現,經歷了設定、形成、實踐,故事到此尚未結束,還有夢境擴散的後續效應,將在後文詳談。先談正面效應,巴神父提出織布中有泰雅族的文字之後,學界有支持與不支持等二種態度。不支持的如中央研究院,支持的如白榮詮(2018)的〈泰雅族傳統織布:隱藏的密碼與科學〉一文,完全接受巴神父的文字說,照單全收,相當尊重揭密織布的說法,相信織布符號有圖案以外的意義,但並未論述何以是文字,只是轉述了巴神父的想法並認其為真,同時提及1999年921地震之後,野桐工坊創辦人尤瑪.達陸回輔仁大學與長期關注服飾文化與設計的羅麥瑞修女共商,獲該校織品服裝學系協助及原民會經費補助,辦了兩年的「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及設計學程師資培訓計畫」,培訓了16位原住民學員成為部落種子教師,把編織文化傳承下去。2000年,任教輔大織品服裝學系的蔡玉珊,也參與這項培訓計畫,並負責教導「圖案設計與色彩應用」及「原住民傳統織物織紋分析與設計應用」(白榮詮 2018:24)。另外,Bauke Dai’i(2016)寫就「921災後第17個過年:讓部落「碰碰」織布聲繼續響起吧!」談到噶哈巫族:「『碰碰』織布聲中找回民族文化的語言,二年多來,我們培育了20多位族人,讓他們從完全不會織布,到現在能織出許多不同花樣的織帶與布匹。一個族群的傳統服飾可視為該族群最鮮明的象徵符號;不同的族群、居住位置及不同的身分地位,皆可能發展出一套制式的形式,其服飾上的符碼宛如另一種隱晦的語言,更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縮影,一篇含有密碼的古文書。」這個「含有密碼古文書」的認知,也是類似巴神父織布文字理論的說法,都認為圖案不單純只是圖案,還有類似語言表意的功能。
夢想實踐生活之中,不只輔大、新北烏來編織班及博物館展覽,還有「路標」(道路里程指標)。2019年底,桃園市復興區桃118市道的公里數指標,出現了巴神父所發現的泰雅族數字。施工單位將巴神父的這套說法,應用在道路指標上,因為他們認為這符號具有部落特色與文化創意。施工單位對於符號是否代表泰雅族數字,並不在意,從網路查有資料如此說,就相信並直接使用。
於是,巴神父的泰雅數字符號,分別出現在桃園市復興區三民天主教堂入口牌樓、新北市烏來區博物館內的展示、新北市烏來區織布婦女之織品以及桃園市復興區桃118市道的道路公里數指示牌。現實情境,文字數字出書後,少人閱讀;展示部落周邊,族人無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字數字卻成了日常的真實,活化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視覺訊號,置入生活脈絡之中,這個夢是否持續發酵、影響部落文化,有待觀察。
IV.文字壯大了自我
巴神父對泰雅族的熱愛與無私的奉獻,令人尊重與景仰,不因是外來者而先入為主地認為怎麼可能是內部文化創生的源頭,也不因是傳教者而認為均是源自宗教發展的利害考量,而貶抑之。本文係基於對一段異文化交會的過程與所產生的變化感到興趣,想要了解西方文明與部落文化遭逢時,彼此互動的狀況與各自發生的變化,及其變化背後的原因。特別是,這段文化交會的場景,是發生在對「文字」的美麗想像。
孫大川在《久久酒一次》一書提及,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是容易遺忘的。他說記憶中,母親對歷來活躍在臺灣歷史舞臺的「主角們」,很少仇視或批評。她總覺得自己的民族是落後的,是應該向進步的社會開放的(1991:18)。也就是說,有文字的族群,是進步的,是不易被遺忘的。一個族群有自己的文字,就會讓人感覺高人一等,是文明的象徵嗎?族人或神父也真的這樣想像或陷入此種迷思?對此,在巴神父的著作第17頁,寫序的泰雅族Ciwas Payas3是這樣說的:「發現泰雅織布中有文字,這不僅對今天的泰雅人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對整個世界也是。它甚至可以說是泰雅族的『文化革命』。我很樂見這樣的發現。並且,我們將有一個重新認識自己什麼是泰雅族人的機會,然後也才活得像個泰雅族人。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驕傲地宣稱自己是泰雅族人。」
書中第18頁,巴神父也這麼說:「泰雅文化這麼美而重要,如果你們泰雅族人自己都不認識、不珍惜,我相信你們的祖先會非常傷心與失望。那些終其一生都在織布的女性祖靈,更會因此哭泣到死。」不過,還不只這樣,其實巴神父對泰雅族的愛與迷戀,讓他在書中第22頁,把泰雅族的起源,拉升到5、6千年之遠(因男女都有紋面之故),並從文字上,與閃語族的關係連結在一起,甚至在族群起源神話上,也連結基督教的說法,如稱閃語族群稱上帝是石頭,而以色列人是石頭之子,這個泰雅族神話所說的族群起源於石生說是一致。巴神父之所以這麼說,是把泰雅族放在一個世界的架構,而不只是臺灣一個孤立的小島上,甚至是古文明的高度來審視,不是單純19、20世紀的一個地區部落而已。可見,在他心中,透過文字,能讓泰雅族與古文明的主要族群或遍布世界的基督宗教有所連結,從織布中的「文字」,讓族群不要小看自己。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人慎重其事地看待文字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性。原住民並不是沒有所謂的紀事系統,身處視「文字」為「文明」的時代裡,擁有自己的文字記載系統,可能是成為「自我決定行動者」(self-determining agents)的第一步(張耀宗 2006:205)。林曉霞指出巴神父一生在泰雅族部落的文字研究,給予整理與紀錄,是期盼泰雅族人能因文字的發現,建立族群的尊嚴和信心,不再以自己的語言為恥,從此昂首闊步,他期盼能有更多人投人,為泰雅族語注入活水,保存泰雅族文字這個無價的寶藏(2016:5-10)。
相似之例,也出現在東南亞有接受深刻基督宗教影響的族群,例如Hmong族的傳說中,他們曾有文字,但遠古祖先在黃河以北被漢族驅趕時,為了渡河,文字不幸被丟落在河裡(Hudspetsh 1937)。文字失傳之後,Hmong婦女以刺繡與蠟染,將文字寫在織品上,但隨著時間而淡忘(Yang 1992: 263)。後來,知名傳教士英國倫敦循道公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師Samuel Pollard(柏格里)為了翻譯經文而設計一套羅馬拼音文字,受到Hmong的歡迎,也因而看到族群的光明與希望(謝世忠 2004b:198-199;Smalley 1990: 149-150;Tapp 1989: 81)。
不過,巴神父發現泰雅族織布中有文字,這樣的文字夢並未引起在地族人太多的關注與興趣。筆者認為主要是傳統上,泰雅族人歷史與文化,本自以口耳相傳,且允許依情境及生命經驗做些改變,因而口傳的文化內涵相當豐富,例如吟唱(mlhuw)承載著過去的歷史與文化,讓族人引以為傲,口傳是過往傳播與溝通主要方式;且在泰雅族人的傳說之中,也並未提及文字,以致族人對神父發現泰雅族有文字一說,顯得較為無感。
V.文/數字的再詮釋
現實生活中,美夢有可能成真,但也有如夢幻難以成真。夢幻與現實的對話,呈現多元交織的複雜發展。巴神父在出書之前,曾將文稿及照片送中央研究院語言學者審查,因難以舉証及未見客觀系統論述,而被否決。接著他也曾請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者,以及臺灣原住民族事務最高的行政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出版,但經審查要求巴神父將文稿中教會版的羅馬拼音修改成教育部之版本,巴神父未予同意,因而與行政部門的合作未成。在他書中第19頁的序言,一位國立中正大學語言研究所的主任何德華(Victoria Rau)即說,這本書並非傳統語言學研究的著作,而比較是民族誌式對符號與意義的描述與分析,且作者對希臘語、希伯來語有深固的基礎。
筆者在復興區泰雅族部落長大,兒時常見巴神父現身部落的教堂與住家附近,巴神父遇到不熟的族人,通常第一句話會以泰雅族語詢問:ima lalu su’?(意為:你叫什麼名字),如果你沒有回答泰雅族的名字,他會進一步關心問:ungat lalu su Atayal ga?(意為:你沒有泰雅族的名字?)巴神父希望泰雅族人要知道自己是誰,學說泰雅族語對鞏固自我認同是相當重要。少數族人知道巴神父從織布中發現泰雅族有文字,但不去批駁,一來是因他是外來神職人員,本具一定的權威,又泰雅族語說的比族人還流利,讓人敬佩;二來是將泰雅族傳承下來的織紋,與埃及文明有連結,讓族人感知自己族群是這樣的「偉大」,意即我族文化相較他族是進步與文明的。原來從泰雅族的織布中可證成泰雅族早有文字,讓人可以對外宣稱泰雅族有文字,文化內涵可與世界古文明接軌,族人不刻意否認與其他古文明有關聯。
傳統上,泰雅族女性通過織布考驗,始具備象徵成年的紋面資格。織布技藝是族人對於婦女是否具智慧與才華的判別依據。對織藝精湛且具創造力的婦女,族人會豎起姆指說:「blaq lay qba’ nya」4,(意即:她是個手很靈巧、聰慧有才的女人);反之,則會說:「mqsuqi’ cikay」5,(意即:有點笨拙的女人)。婦女織紋是允許承襲與創造,對於自己的織品,總有故事可分享。因而,巴神父的文字夢,與他與一位泰雅族婦女的對話有關。那位婦女告訴巴神父說:織布裡有bbiru’,而巴神父理解bbiru’的意思是「文字」,但筆者以為,在語言使用上,bbiru’一詞常有多重指涉,可指稱書畫寫字,不一定專指文字或寫字,也有畫圖之意。當這位婦女說織布裡有bbiru’時,有可能是指圖案紋路,並沒有明講說這就是泰雅族的文字,但巴神父將圖案紋路理解成等同或接近文字,於是源於對文字語言認知的差異,一個美麗的誤解,成就了一場美夢。然而,精通泰雅語的巴神父,為什麼還會誤解?對此,筆者認為語言還是必須回到生活脈絡,且口傳族群的詞彙內涵原本就豐富多元,外人學得再精深,難免會對有些詞彙,不一定能完全理解。
另外,筆者與泰雅族織布的婦女閒談時,對於織布的織紋可能是泰雅族的數字及文字,大部分的回答都是「不清楚」。婦女說織布時,口中所講的1234是指織布的順序,會以泰雅族語“qutux, sazing, cyugal, payat,……”,意即順序是第1、第2、第3、第4。也有婦女認為所謂的數字是在學習織布時,透過老師口傳的順序1234或2423類的術語,因此誤當成數字來解碼。因而巴神父將婦女口述順序,視為泰雅族的數字。這可能也是一種創舉,我們不能否認他的創舉,類似羅馬數字I II III IV……,他從織紋圖像解釋這些為1234,與他的所學及背景有關。
雖然多數復興區的族人不知道這套泰雅族數字,但在遠處的新北市烏來區的泰雅族編織班成員,卻成為織布文字的粉絲、追隨者。她們在烏來區公所積極協助成立織布工作坊6,曾漂洋過海到日本、泰國取經,學習不同地區織布精湛的技法,也參與輔大的織布培訓,從中了解巴神父從傳統泰雅族織布中發現了文字,更是與自身族群文化貼近,因而曾經親自到復興區的天主堂向巴神父請益。何以烏來區的泰雅族婦女積極地到各處去學習?主要是烏來區是觀光勝地,以發展異族觀光為主軸,山地藝品是吸引觀光客要素之一(謝世忠 1994a:43-46)。織布具泰雅族群特色,正可做為與其他族群區別的特色藝品。觀光客到了富泰雅族群特色的觀光區,織布即成為伴手禮最佳選擇,也是到此一遊最好的見證。遊客會慕名而來,帶回這具族群特色的編織物,但也有對此一無所知的遊客,卻因織品有故事而被打動,賦予編織物故事鄉,更容易成為受青睞的伴手禮。(圖3)

圖3 新北市烏來區婦女於2000年親自至三民天主堂向巴神父請益織紋中的泰雅族文字。
(圖片來源:新北市烏來區達卡工坊高林美鳳提供,2019/6/22)
異族觀光係指以被訪地區居民及其工藝品之「異文化情調」(cultural exoticism)特性為觀光吸引力(謝世忠 2004a:175;van den Berghe and Keyes 1984: 314)。泰雅族的編織技藝在臺灣原住民族群中名聞遐邇,為了增加織品特色,加入「傳統」文化要素,「傳統」在觀光情境中,往往是會被再創造、再修整,或再詮釋,才能符合短暫而表面之觀光交易上的需要(謝世忠 1994b:3)。為創造織布的價值,婦女們積極尋找傳統要素,並賦予故事,讓觀光客愛不釋手。在推廣或銷售織布成品時,若能強調其中文字符號的特殊性,吸引遊客購買,自是有效的行銷手法。商品在觀光地區行銷需要賦予故事,婦女們便積極尋找傳統要素,讓商品有故事,觀光客也更愛不釋手,也就提升了觀光收益。
前述提及復興區少數族人知道巴神父的發現,但不完全了解其說法。值得一提,復興區也是假日遊客如織的觀光區,也有婦女成立織布工作坊,但織布婦女並未如烏來區婦女將巴神父發現的文字應用在織布裡。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復興區並非以異族觀光特質建置觀光吸引力,看不見主要景點販售婦女織品;二是福佬語有句話說「近廟欺神」,「距離」是美夢能否成真的重要因素,「近」往往就不是夢,只看到現實,「遠」反而容易讓美夢成真,因為「遠」來和尚會唸經,例如,「遠」在烏來,或其他地區的泰雅族人,反而容易相信泰雅族的織布中是有文字的。這也是另一個有趣的「文字」與「距離」的弔詭現象。
2019年筆者曾參觀新北市烏來區博物館,館內常設展以泰雅族婦女織布為主軸,收藏與展示各地區精美的泰雅族織布,亦將織布相關元素及內涵,做為展示內容。在該館服務十餘年的導覽人員表示,館方曾把巴神父從織布發現的數字製成展版,置於一樓顯眼處,並向觀光客解說隱藏在織布中泰雅族數字,有不少參訪的觀光客感到驚奇與好奇,但展示約僅2年即被撤換,主因有人認為口述才是泰雅族的傳統,是否真有文字,並未獲得普遍認可。
2019年2月,桃園市復興區桃118市道的公里數指標,也出現了巴神父所發現的泰雅族數字。當地大部分族人不清楚所畫為何?筆者的親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好奇的問我:「我家路口最近放置了一面牌子,上面的圖案不知是什麼意思」。經向施工單位桃園市政府工務局養公處了解,並詢問工程設計單位,原來設計單位為了能做出有特色的道路指示牌,於是從網路蒐尋,看到這些符號以前曾使用在新北市烏來區泰雅博物館展版及當地公共設施的道路牆面,於是安心用做為公里數的指示牌,不經刻意解說,族人或觀光客是無感的。但運用在觀光場域時,導覽者可以順勢運用,反而成了述說故事的素材。(圖4)

圖4 2019年初於桃園市復興區桃118羅馬公路設置公里數之指示牌代表「55」,係使用巴神父發現的數字。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19/1/16)
有趣的是,有族人淡淡表示:「沒人懂、沒人教,讓人都看不懂,放在馬路上應該要讓用路人看得懂圖案到底是什麼意義」、「沒有中文標示輔助閱讀,無法讓人了解巴神父的研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很可惜」。族人雖不知這是泰雅族的數字,但知道是巴神父的心血與發現時,族人卻反過來認為,學校可以把這當成教材,教導孩子來認識與了解。同樣地,泰雅族數字佈置在神聖的天主教堂裡,從族人生活信仰中心,提醒族人不要忘記自己的語言。但詢問教友時,多數並不知道教堂內所貼上圖案的意義。在復興區成立工作坊的婦女也表示,為了使織品與他人不同,通常會加進文化元素與發揮創意,但他們不強調這是泰雅族的數字。無論從道路公里數或織品中,泰雅族人未必了解織紋的意義,不過,卻也能包容,讓新創的元素加入泰雅族文化內涵。
VI.結論
傳教士在面對土著文化時,有相關研究指出有「傳教士迷思」,即可能極端否定或極度肯定原住民文化兩種。前者是積極去土著化,而以現代文明改造、替代之;而後者則是企圖用現代知識,嘗試重新發現古老文化價值,去補充、去肯定。有認為土著文化一文不值、看不起,也有說不得了、很偉大。一個可能過於鄙夷、一個過於興奮。然而,這二種論述或不免流於「過度想像」,都在證明心中的想像是對的,或許不符真實,未能充分理解及詮釋原住民。但,這都是一段曾經發生過的事實。
巴神父是筆者熟識的一位長輩,對他尊敬有加,因他熱心奉獻關心泰雅族人,無比真誠的學習泰雅族語與文化。筆者審視他的文字發現,並無不敬之意,純粹想了解異文化交流時,對在地語言傳承的影響與文化的變遷。筆者將巴神父發現泰雅族有文字,比喻成一場文字的奇幻之旅。文字奇幻之旅,來自於他過去的生活經驗與所學所知的歷史觀、世界觀、宗教觀,或西方觀點,觀看與認知泰雅族。這是否是不證自明的前提?還是,這只是一個主觀的設定,上帝之手,一切從這裡開始?可由讀者、族人各持見解。
筆者對於巴神父從織布圖紋中發現泰雅族文字與文化關連的論述中,並不以是否被教友、族人、學界否認或接受為討論重點,而是放在「做」這件事(by doing this),族人見到一位局外人朝著局內人的文化核心前進,成了比泰雅族人更像泰雅族的在地人。族人對於巴神父不斷提醒族人要學泰雅族語,甚至成為族語的教導者,敬佩有加,對其發現泰雅族有文字,不論其真實與否,然而對他重新發現、詮釋與再造泰雅族傳統文化的努力給予肯定。究竟文字的夢是真是假?隨著巴神父退休返回義大利之後,留給後人繼續研究。但重要的是,如前文提及,一個可能是外來者詮釋、孵育出的神話,成了局內人的日常真實,夢想是否持續在現實生活中擴散,留待觀察。(圖5)

圖5 巴神父退休後自義大利回訪臺灣,筆者2016年於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遇到巴神父與羅麥瑞修女。
(圖片來源:李慧慧提供,2016/3/4)
附註
[1]1994年由教育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李壬癸教授編訂「中國語文臺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並函頒實施,1996年中央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後,將族語復振列為施政重點,族語教材的編纂自此從未間斷。在各方努力下,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頒布施行,原住民族語成為國家語言,並在全國設置「族語推廣員」,期把失落的族語找回來。
[2]原稱桃園縣復興鄉。日治時期屬於新竹州大溪郡蕃地,1945年改隸為新竹縣大溪區角板鄉,隔年實施地方自治,角板鄉劃歸桃園縣,1954年10月31日,角板山改名為「復興」鄉,沿用至今。2015年12月25日桃園市升格直轄市,改稱桃園市復興區(復興鄉公所 2014:325)。
[3]Ciwas Payas是桃園市復興區泰雅族人,全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目前任教於復興區長興國小。
[4]blaq lay qba’ ny a在泰雅語中,blaq是指好,lay是強調的語助詞,qba’是手,整句原意指手很靈巧,故有延伸因為聰慧,手才靈巧有才華。
[5]mqsuqi’ cikay,mqsuqi’指緩慢,cikay是一點,因為不太聰明以致動作慢了一點。
[6]1995年行政院文建會提倡文化產業與社區總體營造,手工藝在政府政策輔導下,重啟文化產業,成為族群文化復振的亮點,紛紛成立工作坊(曾秋馨 2013:48-50)。
引用書目
巴瑞齡
2009 〈原住民語文字化的難題發微〉。刊於《語文與語文教育的展望》。周慶華編,頁45-58。臺北:秀威。
巴義慈(Fr. Alberto Papa O.F.M.)
1986 《泰雅爾語文法》。臺北:安通社會學出版出版。
1993 《認識泰雅爾母語》。桃園:桃園縣復興鄉三民天主堂。
1995 《泰雅爾語研習初級本教材,第一冊》。臺北:思高聖經學出版。
1999a 《泰雅族母語初級讀本──泰雅爾字母輔助教材》。桃園:桃園縣政府。
1999b 《泰雅族母語初級讀本》。桃園:三民十字架堂泰雅爾語研究工作室。
2000a 《泰雅爾語研習初級基本教材,第二冊》。桃園:三民十字架堂泰雅爾語研究工作室。
2000b 《泰雅爾語字母輔助教材簡介手冊》。臺北:至潔。
2013 Picture Writings on Atayal Tattooed Women’s Clothes in Taiwan. Taiwan: Gabriel Printing Co., LTD Press.
白榮詮
2018 〈泰雅族傳統織布:隱藏的密碼與科學〉。《科學研習》57:20-27。
李壬癸
2002 〈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臺灣史研究》9(2):1-68。
李懿宸
2010 《臺灣原住民部落教堂視覺呈現之圖像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
林曉霞
2016 〈泰雅文化解碼人──義大利巴義慈神父〉。《文化桃園》4:5-10。
孫大川
1991 《久久酒一次》。臺北:張老師出版社。
2000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學。
賀安娟
1998 〈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1624~1662〉。《臺北文獻》125:81-119。
黃秀仍
2005 〈荷據時代臺灣原住民語言政策及教育〉。《遠東學報》22(1):49-56。
張耀宗
2006 〈文化差異、民族認同與原住民教育〉。《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6:195-214。
曾秋馨
2013 《織布文化與口傳文學:以泛泰雅族群為主》。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民間文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復興鄉公所
2014 《桃園縣復興鄉志增修》。桃園:復興鄉公所。
謝世忠
1994a 《「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臺北:自立。
1994b 〈觀光過程與「傳統」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刊於《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頁1-18。臺北:文建會。
2004a 〈觀光活動、文化傳承的塑模、與族群意識──烏來泰雅族Daiyan認同的個案研究〉。刊於《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謝世忠著,頁175-19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4b 〈Hmong/苗族的生存機制─力量再生的傳統與傳統力量的再生〉。刊於《國族論述──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謝世忠著,頁195-20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Bauke Dai’i(潘正浩)
2016 〈「921災後第17個過年:讓部落「碰碰」織布聲繼續響起吧!」〉。「MATA TAIWAN」,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83184,83184#msg-83184,2020年6月26日上線。
Hudspeth, Will Harrison
1937 Stone-gateway and the Flowery Miao. London: The Cargate Press.
Sing ’Olam(星.歐拉姆)
201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推動族語與傳道之行動〉。《原教界》51:18-21。
Smalley, William A. et al.
1990 Mother of Writ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Hmong Messianic Scri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pp, Nicholas
1989 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 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and Charles F. Keyes
1984 Introduction: Tourism and Re-created Ethni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1: 343-352.
Yang, Dao
1992 The Hmong: Enduring Traditions, In Minority Cultures of Laos. In Minority Cultures of Laos: Kammu, Lua', Lahu, Hmong and Mien. Judy Lewis, ed. Pp: 249-326. Rancho Cordova, CA: Southeast Asia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