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像山一樣思考
文獻評介
第41期
2019/12
文/林益仁

林益仁
生態人文研究者。生態學(ecology)的字根eco-,其希臘文的原文為「家」的意思。我的學術生涯從研究動物生態學開始,曾在阿里山研究高山鼠類的棲地(家)、屏東霧台鄉的魯凱族聖地小鬼湖研究山羌的活動範圍(家)。後來,因遇到魯凱族的獵人,而對原住民文化視野中的「家」產生興趣,並由此延伸出二十世紀末馬告國家公園爭議中對泰雅族傳統領域(家)的探索。此外,我的博士論文從社會文化的脈絡探討宗教徒在自然中的價值與態度建構,試圖在深層生態學與政治生態學的不同路數中,找到一條可以多元陳「家」的道路。目前,在臺北醫學大學的醫學人文研究所任教,嘗試開拓生態醫學的研究新課題。
我先來講一段往事。

|
圖1:莫拉克災後的山河景象。(資料來源:林益仁提供。)
|
2010年夏天,我曾經到澳洲開一個蠻特別的會議,這是第二屆的荒野律法(wild Law)與大地法理學(Earth Jurisprudence)大會,那次的主題訂為「守護那火」(Keeping the Fire)。荒野律法與大地法理學是在澳洲發展出來,從深層生態學的理念挑戰以人類為中心的法律思維與制度。在那個會議中,我的人類學家好友,《丁哥使我們成為人:澳洲原住民文化中的生命與土地》(Dingo Makes Us Human: Life and Land in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Culture)一書的作者Deborah Bird Rose教授跟我說:「你應該去認識主題演說者John Seed,他是一個非常關心森林,重視原住民權利的澳洲生態環保人士。」同時,他也是《像山一樣的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這本書的編者。這本書的另一位編者是國際知名的深層生態學思想家Arne Naess。

|
圖2:屏東霧台鄉在莫拉克災後的景象,John告訴我他從未看過如此震撼的大地威力。(資料來源:林益仁提供。)
|
後來,我果真有機會與John同車。在一起去原住民土地抗爭地點Sandon Point Aboriginal Tent Embassy的營火會路上彼此認識,並且相談甚歡。我感覺他的想法很有啟發性,很值得我們學習與互動,所以就在隔年邀請他到臺灣來參加臺灣荒野協會的年會。他2011年在臺灣的行程,我帶他到莫拉克風災的重建地區,並且關心尖石鄉泰雅族反水庫的行動。交談當中,我問了他一些切身的問題。我說,因為「像山一樣的思考」常常給我一種比較靈性且脫離紅塵世俗的感覺,但是我看John Seed又不單單只是這樣。
從生態看人群之間的衝突

|
圖3:在旅程中,我與John有許多的機會進行深刻對話。(資料來源:林益仁提供。)
|
在我的觀察中,他不僅重視靈性修為,更是一個入世的社會運動者,像是在澳洲塔斯馬尼亞省為了拯救熱帶雨林,他就與曾擔任過澳洲綠黨主席Bob Brown一起參與激烈的反水庫抗爭;John非常認同原住民的文化,所以也參與不少協助原住民爭取土地權利的相關社會運動,在臺灣的旅行中更寫下了他的詳細見聞。旅行中,我問他:「你參與這麼多的社會運動都非常基進,在激烈的抗爭中,充滿世俗複雜的政治議題在裡面,但我看你又能像一個宗教者一樣。為什麼?」那幾天我陪著他,發現他晚上都很早就寢,而早上很早起床。他對佛教思想有相當的投入,非常重視心靈的照護,隨時在意培養強韌的內在心靈力量。
我更接著問:「你可以一方面投入在很激烈的政治抗爭,爭取這些權利,可是另一方面又能非常寧靜,你如何知道在什麼時候需要保持一個沉靜的心靈?這兩件事情如何融合起來?沒有衝突嗎?」我之所以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社會運動常常需要歷這些激烈的衝突和對抗。在投入這些事件核心的當下,我都可以感受那種身心的煎熬,就是一方面在政治場合的對抗,另一方面又需要尋求某種心靈的寧靜,如何看待這些事情?我問了這些直接的問題,但他只簡單地回應說:「你或許可以看看這一本書!」就是《像山一樣思考》。在這本書中,他與三位編者中的Joanna Macy一起發展「沮喪與培力」(despair and empowerment)的生態心理學方法,對於社會運動者長期處於感受大地受苦所承受的壓力提供一種療癒的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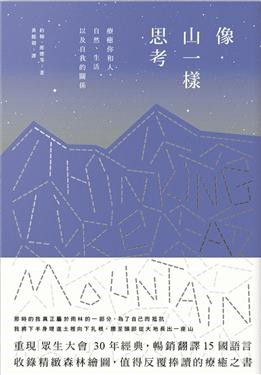
|
圖4:《像山一樣思考》中文譯本的封面。(資料來源:林益仁提供。)
|
在《像山一樣思考》這本書裡,我可以找到一些哲學家、宗教家、詩人,還有一些作家,他們都分別從他們參與的社會抗爭、生態運動裡認真地去反省他們的內在,屬於心靈的部分。這本書的書名起源自Aldo Leopold的一本書。Leopold的盛名,如果關心生態、參與生態保育運動的人,對這位美國的生態保育學家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其實,「像山一樣的思考」這句話就是從這一本書裡面所引出。Aldo Leopold在書裡面講了一個故事,他和一群獵人從山頭往下開槍,企圖獵殺一群正在過小溪的狼群,開槍後,他們衝下山頭,小狼都順利逃跑,只剩下一頭中槍倒在地上的母狼,Aldo Leopold靠近的時候,那一頭母狼還沒有死掉,Aldo Leopold在書中描述說當他看到她銳利的眼神,就在他的眼前,逐漸消逝的霎那,震動了他的心弦。他非常傳神地描述了那個眼神,A Fierce Green Fire(一朵兇猛的綠光)。應該是在幾秒鐘的時間,那個眼神就在他的眼前消逝了。
後來的學者研究他寫的這一段故事,認為那是Aldo Leopold非常重要的思想轉折點。在當下,他從一個以人類為本位將自然視為自然資源、強調生態資源必須善加利用的學者,轉而進入到一種與生命共存較為深層的哲學層次思考,直接挑戰我們人類是否應該輕易地就擅奪另外一個物種的生命,同時深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與角色。他講了一段歷史事實,他說在那個年代,狼與山獅這些猛獸對大部分美國人而言都是有害的,因為牠們會傷害家畜,即人們寶貴的私有財產。所以,看到狼就獵殺是天經地義的事。甚至,美國農業部還發放毒藥毒殺這些動物。不過,Aldo Leopold提出一個命題,就是:當一座山沒有狼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後來,他做了一個在自然保育學界非常經典的實證研究,指出當狼消失以後,因為沒有天敵,鹿變得很多,接下來草就幾乎被鹿吃光,然後山就開始逐漸禿掉。更慘的是,當一座山禿掉以後,鹿隻將跟著死亡。為了人類自身的絕對利益,傷害狼群的結果,終將傷害自己,這是他留給後世非常重要的生態研究成果。Aldo Leopold從生態學物物相關(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的道理,悟出人類必須對自利行為反省的理由。避免與療癒在自然中造成傷害貴在人類有這種自省與節制的能力。
因此,《像山一樣思考》想要表達的是一種生態思維,每一個物種和其他物種都有某種關聯性。我們能不能那麼輕易地去取人類以外物種的生命?或許取其他物種生命的時候是為了我們的好處,但同時,我們必須認真思考跟那個物種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其實,我分享這段往事,不是單單要介紹一些西方生態學家的思想。我其實更想做的是,這些思想如何在臺灣的文化脈絡中和我們進行對話與建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是盤旋在我心中許久的一個課題,這也是一個關於衝突與生存的課題。
從原民狩獵文化得到的啟示
再講一個故事。
有一年,新竹尖石的田埔部落耆老Pagung Tomi邀集了另一位獵人耆老Yudas Silan在和解廣場示範與講解了泰雅族的狩獵文化與在地的故事。和解(Sbalay)廣場的設立,是因為紀念一次在日據時代的狩獵誤擊事件的和解,這個誤擊讓Mknazi與Mrqwang的兩個支群因此產生衝突,並且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在此所凸顯的狩獵議題,不僅是一個維生的行動,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
土肉桂(Cinnamomoum osmophloeum Kanehira),是一種香料植物,泰雅族人稱為hom,是他們重要的食材。土肉桂,不僅吸引泰雅族人,也吸引其他動物,所以當結實的季節,松鼠、飛鼠、果子貍、山羌等動物都會前來覓食。土肉桂林,是善於觀察的泰雅人布置陷阱狩獵的地點,在取得土肉桂樹葉的同時,這裡也提供了必需的動物性蛋白質。因此,辨認與認得土肉桂樹生長的地方,便是重要的生存知識。這些知識都是田埔部落的Yudas Silan耆老在課程中娓娓道出的內容。他帶我們走入森林,找到土肉桂樹,並且示範如何在樹下裝設陷阱,他一再強調,狩獵不僅要懂獸跡,也要辨認植物的用途。在製作陷阱的同時,他找到動物的腳印以及行走的路線,指出陷阱與腳印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就地取得做陷阱的材料,過程中還得注意不能破壞現地的環境。
原住民狩獵,是一種傳統的生活技術。這種技術,不僅需要搭配細膩的生態觀察,還受到狩獵文化禁忌與社會規範的約束,包括獵場經營的傳統領域概念。傳統上,不用槍的獵人,必定會是一個博學且技術高超的生態學家,因為他不僅懂得動物,還要認識植物,在山林中求生也必須知道物候(phenology),瞭解生態系統內的物種互動關係。獵人的行動背後受到養家糊口需求的約束,如果他回應了此一約束,必然也是個遵守文化規矩的人。此外,泰雅族有群獵的習慣,根據口傳獵人們要一起進入山林狩獵時,必定先進行一個Sbalay的和解儀式,意思是將各人彼此之間的恩怨過節在進入森林之前,先行和解,否則在狩獵面對兇險的情況下則無法團結。在泰雅的生命觀中,死後,男人必須是合格的獵人才能走過彩虹橋,道理就在此。
在那次的經驗中,我們見證了耆老的豐富生態技術、知識與道德觀,以及歷史事件。最後,我們還用土肉桂葉烤雞。傳統上,應是雉雞類的獵物,包括藍腹鷴與深山竹雞等,但我們技術不好又擔心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只能用肉雞取代。所幸,林下捕捉到的松鼠後來製成了「三杯鼠」。這個土肉桂食物備製活動,深刻地體現了泰雅族文化的重要側面。森林,不僅是一個生態體系,在許多故事與口述歷史的連結下,這個地景呈現了一群人生活的整體面貌,而其中的連結橋梁則是耆老的經驗與知識。
關於狩獵,在一次的訪談中,泰雅耆老Masa跟我提到泰雅族的終末觀。他說,當一個好的獵人死去時,他的靈將會跟死去的獵狗以及獵物的靈一起走過彩虹靈橋。當下,我深感不解,如果是獵狗我可以理解,因為牠是忠實的夥伴,但至於獵物我就真的不懂。為何生前打得非得你死我活的獵人與山豬的關係在死後,會一起度過彩虹橋呢?Masa長老笑笑地說,林老師,泰雅族不是以敵對的關係來看待山豬與獵人。反之,在激烈的生死搏鬥當中都在決定誰會變成誰的食物,所以彼此為對方食物的關係是一種依賴關係,而非僅敵對而已。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中還有許多關於衝突的故事,其中泰雅族Mgaga的習俗更是經典。這個詞一般誤譯成「出草」,被認為是野蠻、報復、血腥等不文明的象徵。但它的本意卻是執行Gaga,亦即落實倫理道德規範。可惜的是,這個深奧的生態道理被外來殖民者簡化與扭曲為「砍人頭」,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因為單單只是砍人頭,實在無法解釋這個人頭被帶回後,泰雅族人還必須恭敬地將它放在骨頭架上,按時餵食,不可怠慢的行為。事實上根據口述歷史,Mgaga是發生於部落之間重大的歧見無法解決,例如獵場範圍各執己意時,部落尋求天意的神聖儀式。其作法是部落各派勇士出去,誰先取一個陌生人頭回來,即為天意,意思是上天的意思與該部落的想法一致。這個Mgaga的神聖儀式因此可以消弭一場嚴重的部落戰爭,但是卻有人因此而犧牲了。泰雅族人因此視此犧牲的人為新加入的夥伴力量,並非敵人。
其實,在泰雅族的世界觀裡,人死並非終結,尚有靈魂存在。所以,一個人頭被帶回,意味著這個人頭的靈魂加入此一部落的聯盟,成為「自己人」了!這個道理和狩獵的獵物頭骨與下巴骨被保存並整齊排列在家屋角落一樣。這個動作象徵了這個外族與獵物成為自己的力量。這是一種自然界殘酷但卻互相依賴的生存道理,雖然演化論提出者達爾文所在的英國維多利亞人們稱之為自然的「血牙腥爪」(red in teeth and claws)。
這個自然的面貌是事實,也很難否認。這個自然的面貌清楚地表達在臺灣的原住民文化中,是生態倫理中較難融入現代所謂文明的人類社會的概念。但生態哲學家Holmes Rolston III教授卻指出,在「血牙腥爪」(red in teeth and claws)自然演化史的傳統理解之外,較鮮為人知的相搭面貌,這是一種強調「照顧」(caring)生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展延、多元、保育以及豐富等行動。這個內涵很有力地且充分地表達在原住民文化裡對於人頭架與獵物骨頭排列的動作中。雖然殘酷,但卻透露出「照顧」的生態意義。
小結:生態照顧視野下的衝突
原民狩獵文化看似殘酷,卻反映了一種家園「照顧」(care)的觀念,強調有機體彼此之間在環境中生存的互動關係。想想前面所提部落衝突與狩獵的行動,都是起之於此。基本上,「照顧」一個生命體起於基本生存條件的滿足,以食衣住行為主,從最根本的自我保護出發,個體的毛皮可視為是一種「照顧」的記號。自我保護,是一種不斷調整後的適應狀態,不同的生命體在不斷彼此互相調整的過程中,整體性地網絡化於一個彼此依存的生態體系中,而形成一個與它者彼此互相需求的支持系統。狩獵與Mgaga背後都有此含意。
此外,在一個生態系統中,個體會被強制不斷地調整自己以求適應環境,因此有必要關注它者的動態。捕獵者必須「照顧」獵物,這是為了長期求生與可持續的食物供給;相對的,獵物也「照顧」了捕獵者,但卻是生存與犧牲的抉擇。兩者所在的位置不同,但都參與在「照顧」的生態行動中,捕獵與逃脫似乎是一體的兩面。此外,它們也同時「照顧」自己的幼獸與家族成員,這是為了基因的延續。「照顧」,無可避免必須認真考慮自我與它者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千變萬化,有些是我們熟悉可以接受的,但有些陌生也難以接受。Rolston教授的生態倫理論述,在相當程度上提供了對於Mgaga的生態解釋,也提供原住民狩獵議題寬廣的思考,當然也對於自然與人類社會中的衝突提供另一種視野,值得繼續深入的探討。它者,不是敵人。常常,它是我們自己。回到文前的澳洲之旅以及好友Rose從澳洲原民哲學中所提到的澳洲野狗「丁哥」使我們成為人,不正也是回應這樣的道理嗎?這是像山一樣的思考,值得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