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遇在Kucapungane:導讀《古查布鞍遷村一年》
新書視窗
第30期
2016/12
文/阮俊達
為了重建家園,一個風災後流離失所的部落,能展現出多大的韌性?一位來自都市的研究者,又如何在有限時間內記錄這段過程,並深刻體會田野間生命與生命的碰撞?
部落的一年:日常是各種關係的總體性
《古查布鞍遷村一年》記述了古查布鞍(Kucapungane,魯凱語「雲豹的傳人」之意,漢名好茶部落)族人經歷2007年聖帕颱風與2009年莫拉克颱風侵襲後,於2010年底輾轉遷徙至禮納里永久屋定居,入住一年之間,部落的日常生活與大小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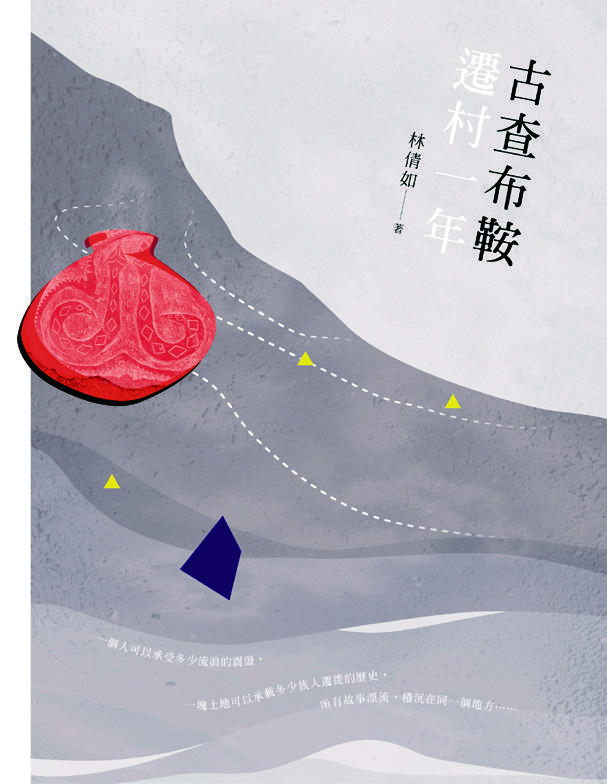
林倩如《古查布鞍遷村一年》書封(圖片來源/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林倩如透過細膩的田野參與觀察與訪談,敏銳勾勒出居民災後搬遷歷程中的心境轉折:遷移之初,族人們告別了軍營克難而缺乏隱私的安置處所,鎮日蝸居屋內整理記憶、舔舐傷口,到逐漸熟悉新環境,開始踏出家門烤火、煮食、做工、歌唱,藉著人與人的團聚和互動,而得以舒展身心;此後,隨著重返舊部落尋根、部落文創班的啟動、祭典恢復舉辦、乃至於家戶空間及聚落入口意象的營造,一個又一個事件堆疊下,部落以緩慢但堅實的步調,重新綻放出生機。
如同倩如所言,正是種種生活中微觀層次的感知與行動,使族人們在新生的永久屋聚落裡重建了社會關係,讓此時此刻的居所真正產生意義。於是,「空間(space)」遂逐漸成為了「地方(place)」──或更白話地說,成為了部落,成為得以安身立命、延續文化的家園。
我們因此知道,任何天災人禍所致的遷村、安置等重建政策,從來便不只是給予土地和房屋就可告一段落(尚不論有無土地產權、房屋品質如何),而是得等到族人調適心情、穩定生活、恢復各種互動關係,和遷居地間「產生與之連結的故事」,傷痕才有機會結痂癒合。我們也因此明白,原鄉部落並非均質、靜態的存在,當中包含家族的、階級的、性別的、世代的…種種差異,面貌各異的族人,每一位都在遷村過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著生命背景與社會條件而有不同的考慮、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這一切,都必須被細緻地理解。
然而,藉由本書的觀察,我們卻同時看見政府對部落真實生活樣貌的陌生,以及官僚體系便宜行事下的粗糙舉措。無論是沒有配套規劃的培訓課程,或是一戶補助十萬元但要求限期完工和事後核銷的「門戶設計方案」,僵硬、片段而對在地需求缺乏完整理解的計畫,實際上可能引起爭議、造成困擾、甚至引發部落內部的文化衝突。透過倩如的文字,我們讀到了溫婉但不失精準的批判。
如此具有深度的書寫,使本書清楚照見當代臺灣原住民部落的複雜性,以及日常情境的多義性。與其他書寫莫拉克災後原鄉重建的第一手報導如《在永久屋裡想家》(2013)、或是政府委託出版品如《百合花開的季節》(2014)相較,作者貼近部落族人感知的主觀敘說,讓一則則生命故事顯得立體而動人。《古查布鞍遷村一年》因此恰可與奧崴尼.卡勒盛(即書中的邱金士邱爸)《消失的國度》(2015)的大歷史書寫互相補充,是認識當代古查布鞍族人流離經驗不可忽略、更難以被替代的一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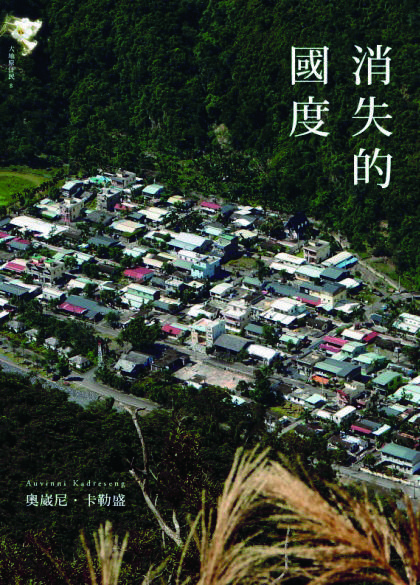
《消失的國度》封面(圖片提供/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
田野是一面鏡子
除了深刻記錄遷村過程外,《古查布鞍遷村一年》的能量還遠遠不只如此。翻開書本,我們跟隨倩如的腳步,順著時間推移,溫熱地感受到她以漢人、女性、都市居民、研究者的外來身分,展開陌生田野旅途的摸索過程。一年之間,從在部落四處晃盪到有了固定互動對象,從高雄屏東當天來回到有了過夜落腳之處,從發散的觀察到開始聚焦訪談,一路上,倩如用日記體完整寫下了田野中的種種難題與困惑。
當中包括進入田野的困難:迷路、酒醉、語言隔閡、或是上山時成為累贅,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該如何調適?如何克服?如何化解尷尬?尤其,身為隻身一人來到部落的年輕女性,遭遇酒攤邀約或言語調侃時,應對的智慧,再再需要謹慎拿捏。
讀來相當令人驚訝的是,倩如近乎鉅細靡遺地敘說了田野中的心情,不管是挫折、憤怒、喜悅、還是淚眼模糊的感動,都一一被以極為主觀、近乎赤裸的筆觸敘說。例如重返舊好茶當夜的酒宴,即使踉蹌返回過夜處,「閉上眼前,手機顯示午夜十二點,下一秒,不醒人事,聽到外頭中壯輩才正興起的酣暢」(頁81),隔日酒醒後仍能詳細寫下前晚將醉時的細節與感觸:
喉辣心燙,遙遠的夢境,靠擁在祖先的懷抱,心噗通噗通擊跳胸口,『記憶就像是透過淚水望出去。』想起托爾斯泰這句話,景框劇烈搖動,不知為何,聽得我淚眼矇矓…(頁79)
正是這樣生動的書寫功力,使讀者對田野中的細節彷彿身歷其境,從而無論是否從事過田野調查工作,都能想像現場的景況。
在部落的時間拉長後,外來者會勢必面臨田野的瓶頸:研究遲遲沒有進展,該怎麼辦?身為不具原民身分的研究者、不是社群裡的一份子(如何成為一份子?),真的有辦法理解部落,以書寫做出貢獻嗎?或更根本地,是否以一廂情願的浪漫想像、甚至是做研究的傲慢姿態,反而給族人帶來困擾?種種自我質疑,成了田野期間反覆出現、揮之不去的陰影。倩如經歷了這樣的研究低潮,困於對自己的懷疑與對族人的承諾,緊繃焦躁,身心失控,終至大病一場,情緒完全陷落而不得不狼狽離開田野地點。然後,一如剛搬遷到禮納里的古查布鞍族人,她也以蝸居的姿態,一面休養,一面靜靜舔舐因自責田野關係混亂、失敗、痛苦而生的傷口。沉澱身心,回望來時路,終於想透「即使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這樣身心投注,不顧一切」(頁218),於是重新整裝上路。
遠離部落現場後的煎熬與反思,讓倩如與自己和解,也與田野這道生命課題和解,並領悟「平地人式的採訪」在部落行不通,「化為答案的不只是嘴巴吐出來的算,(還包括)日常、生活、片語、身體各種片段的總體性」(頁287)。更重要的是,反而在把「做研究」本身放下後,方能直視自己的內心,自在面對與部落族人之間的友誼,而終能詳細描繪部落生活的種種關係。而將這段刻骨銘心的田野歷程化為文字,恰恰是極為真摯的「反身人類學(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書寫實踐。田野正是映照自身的一面鏡子,我們以為自己在看別人,最終卻看見了自己,而且,是以全新的眼光看見了自己。
家的多義性
往返於都市與部落,既追索田野面貌也扣問自我的寫作,使《古查布鞍遷村一年》牽引出「家」的多重意涵。若說家同樣不只是物質的「空間」,而是關係與意義交疊的「地方」,那麼,對作者而言,臺北的家(原本生活的家),高雄的家(就學租屋的家),部落的家(田野期間租屋的家),書寫中先後提及的三個家,都算得上是家嗎?
臺北是作者想要逃避、不願意讓家人煩惱自己的家;高雄是冷漠的暫時棲居之所,甚且被房東「迫遷」;那部落呢?「真際明悟到『部落才是一個家』的動詞意」(頁212)後,所謂的「田野」反倒才是回得去的地方嗎?由此,想要逃離卻又必須回去、是研究對象也是確實居住生活所在的田野現場,產生了弔詭的兩面性,讓人不得不細細思索田野之於研究者自身的豐富意義。
進一步將古查布鞍族人從舊好茶、新好茶、隘寮軍營到禮納里,流離在多處空間下對家的追求,與作者自身對家的經驗相較,多變面貌,多重意義,多元人群交會的家,使的本書不僅僅探討了魯凱族部落對家的理解,更引領著我們思索,當代社會的家可以是什麼模樣?何處又是我們的家?即便書中沒有直接對此進行理論探討,卻依然對這項重要人類學議題提供了有趣的民族誌文本。正是如此,本書作者於2012年發表論文時使用的原書名「《流》becoming─交遇在古查布鞍的那一年」,更顯得動人而饒富意涵。本書揭露的這些故事,正彼此相遇後最珍貴的結晶,正是人與人、人與族群、人與空間,互為主體的深刻對話過程。
貼近部落日常生活的《古查布鞍遷村一年》,推薦給想了解好茶遷村與重建經過的讀者,也推薦給有興趣於思索當代社會中家如何可以為家、部落又如何繼續作為部落的讀者。同時,作為真誠的田野記錄與反思,本書要推薦給人類學的學徒與愛好者,更推薦給所有願意放下過度浪漫的想像、放下自以為是的姿態,真切走進田野碰撞、體會、思考的每一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阮俊達,臺中人,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同時是原住民族運動的參與者及書寫者,碩士論文《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1983-2014)》探討原運三十年來的脈絡和影響,相關著作亦發表於《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臺灣人權學刊》等刊物。穿梭在都會街頭與原鄉田野之間,期望自己能用更貼近土地的頻率來呼吸。